从“三大案”到特朗普“复仇”:美国会出现“白宫魔咒”吗?
- 职场
- 2025-02-20 09:28:07
- 13
执政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加紧推进所谓“复仇议程”。对事上,他上任伊始就推翻了拜登政府颁布的80多项行政令,在移民管理、多元文化和能源转型等多个领域推行截然相反的政策。对人上,从拜登、布林肯和沙利文等政治对手,到司法部、联邦法院和五角大楼的职业官僚,再到第一任期内的下属埃斯珀、博尔顿,特朗普实施了从撤销安全许可、解除特勤局保护到停职解雇不等的“清理”措施。
这些对人措施,有些是为了保证各联邦机构未来将会忠实贯彻自身意志,有些则是纯粹为了剥夺对方享有的礼遇,还有的则兼而有之。在打击对手和惩罚不忠的同时,特朗普还赦免了1500多名 “国会山骚动”的参与者。特朗普的坚定盟友帕姆·邦迪已通过参议院确认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参议院也即将对特朗普的另一名心腹、他提名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人选卡什·帕特尔进行最终表决。在华盛顿,很多人都认为特朗普真有可能对拜登、希拉里和奥巴马等重量级政敌展开调查。特朗普的一系列举动赢得了支持者的欢呼,但也引发了主流媒体的哗然。

特朗普 视觉中国 资料图
美国政治体系中适度的“政治清算”必不可少
特朗普对事对人的做法无疑可以称为政治清算。所谓政治清算,其内涵既包括推翻之前政府的政策路线,也包括清除前任政府任命的政务官员,或者坚定支持前任政府政策的事务官员。
长期以来,政治清算是美国政治体系正常运转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理论上,之所以西方国家要定期举行选举,是为了在国家政策上及时反映主体民意的变化。然而,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要想调整政策路线,只靠总统和副总统这两个民选领导人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必须搭配“政治任命”制度,授权民选官员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在政府中任命相当数量的政务官员。如果政治任命没有足够的广度和深度,民选领导人的权力将不足以有效指挥职业官僚,其结果很可能是由官僚掌握行政部门实权,对民意变化极不敏感,形成傲慢的“有司专治”。
然而,理论上只有“适度”的政治清算才能发挥上述相对积极的作用,“过度”的政治清算则可能适得其反。一方面,对人的政治清算在范围上要适度。广义上的行政机构不仅要承担政治性质工作也就是制定政策,还要承担事务性质工作也就是执行政策,而后者需要经验的积累和技艺的传承。因此,如果行政机构的成员能够忠实执行民选领导人的政策,那么为了行政效率考虑,则不必予以清算。如果强行清算,很可能降低行政效率,甚至导致复杂体系的崩溃。此外,如果民选领导人能够随意撤换行政部门的所有官员,那就意味着前者能够在行政部门内为所欲为,这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因此,现代国家大多会以法律手段来保护职业官僚或者说事务官员的独立性,以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运行。
另一方面,政治清算的力度也要适度,特别是在对人上要留有余地。在美国,与选举周期相伴的政治清算只是剥夺某一政治集团对行政部门的控制权,而不会剥夺其全部影响力和因担任高级行政职务而带来的部分特权。政治清算的温和性也正是让各种政治力量都能接受周期性政治清算、“愿赌服输”的关键。
参考上述理想模式,特朗普当前推行的“复仇议程”显然不是“适度”的政治清算,其在清算范围和力度上都超过“常规”或者强烈展现出这种可能性。其一,特朗普上台后,清除拜登任命的政务官属于天经地义,留任才是不一般的礼遇。但是,特朗普清算范围从一般政务官扩展到了拜登过去按照程序任命的高级事务官,以及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事务官,这包括司法部的很多律师、检察官以及联邦法院的法官。其中,对于司法和执法机构的清算尤其容易引发争议。
第二,特朗普在清算力度上也有些把持不住。目前,特朗普已经取消了身为前总统的拜登的安全许可,还把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由四星上将降格为三星中将,这些“刑上大夫”的做法已经有些出格。如果他未来真的兑现威胁,命令司法部门调查拜登、希拉里甚至奥巴马,并予以定罪判刑,那更是意味着美国政治体制的运行成本将大幅提高,甚至有可能无法继续“照常”运行。
不过,公平地说,对照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上台时的做法,可以看出不能将其推行“复仇议程”和过度政治清算完全归因于特朗普的个人性格。事实上,特朗普的很多做法只不过是照葫芦画瓢。例如,如果说特朗普取消拜登、布林肯和沙利文等人的安全许可是有违常规,但事实上拜登在2021年上台之后就取消了特朗普接触部分机密文件的渠道,理由是他的心理不够稳定,可能泄漏机密信息。事实上,在2016—2024年间,美国反特朗普的政治力量策动了针对特朗普的“三大案”,对其造成了严重的政治伤害。这一经历直接催生了当前特朗普的“复仇议程”。
“三大案”推动美国政治清算极端化
从2017年上台执政到2024年底再次赢得大选,特朗普团队在很长时间内都面临着大量司法诉讼和立法调查,其中影响较大的可以称为“三大案”。
第一大案是“通俄案”。2016年12月,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输掉大选后,奥巴马在执政的尾声指示情报部门就俄罗斯影响美国大选进行调查,这也拉开了“通俄门”调查的序幕。2017年5月,由于时任司法部长塞申斯因自身涉案申请回避,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任命老布什时期的司法部副部长穆勒担任特别检察官,调查“通俄案”。到2019年5月底穆勒辞去特别检察官并解散办公室为止,特朗普竞选团队主席保罗·马纳福特、副主席里奇·盖茨、第一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父子、竞选顾问罗杰·斯通、竞选团队外交政策顾问乔治·帕帕多普洛斯等先后遭到起诉,并先后认罪及被定罪,判刑从14天到7年多不等。包括他们在内,共有34人在调查过程中遭到起诉。然而,除了马纳福特和弗林还涉及洗钱、金融和税务欺诈之外,大部分人的罪名都是妨碍司法、干扰证人和虚假陈述。在司法部于2019年4月公布的最终报告中,结论是并未发现特朗普团队与俄罗斯的共谋或不当行为,即使有接触,可能也不属于刑事犯罪范畴。
第二大案是“颠覆案”。2021年1月6日,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国会山骚动”。事件发生后,特朗普政府内部包括副总统彭斯在内的不少人,均对特朗普鼓动支持者冲击国会山、试图否认和推翻选举结果持强烈不赞同态度。对此,民主党人抓住机会,先是在2021年1月13日推动了第二次弹劾案,未果后又于6月28日由众议院表决建立“1月6日袭击事件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骚动。
“颠覆案”主要涉及三个部分,其一是众议院特别委员会的调查,其引发了纳瓦罗、班农等事发时高级白宫顾问或前顾问“藐视国会”、拒绝作证的起诉,最终两人均被判处4个月监禁,并在走了直至最高法院的一整套司法程序后于2024年上半年开始服刑。调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于2022年12月22日公布,批准对特朗普就犯有妨碍官方程序、密谋欺诈联邦政府、串谋做虚假陈述以及煽动或协助叛乱展开调查。其二是在国会展开调查的同时,由于特朗普在大选结束后试图推翻佐治亚州的选举结果,进而否认大选结果,佐治亚州也展开了对特朗普和另外18人的刑事指控。期间,有4名被告认罪。特朗普本人也一度在2023年8月赴亚特兰大交保以离开拘留所。其三,还有1500名特朗普支持者因参与“国会山骚动”而遭到调查、起诉和判刑。在审理颠覆案期间,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局还因追回保密档案而与特朗普发生争执,导致美国司法部就机密记录处理不当展开调查,联邦调查局还于2022年8月搜查了海湖庄园。
第三大案是“封口费案”。从性质上来说,该案与“通俄案”或者“颠覆案”相比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是直接与特朗普本人相关。此案爆发于2018年1月12日,当时《华尔街日报》披露特朗普通过其律师迈克尔·科恩与艳星斯托米·丹尼尔斯签署保密协议并支付封口费,以阻止后者披露特朗普的婚外情。在该案中,科恩与特朗普集团首席财务官艾伦·威塞尔伯格先后因税务欺诈、虚假陈述等指控被判处监禁半年到3年。最终,就连特朗普本人也未能幸免。在大选角斗正酣的2024年5月30日,纽约州大陪审团判定特朗普34项罪名全部成立。2025年1月,纽约市法院又做出了有罪但无条件释放的判决,让特朗普成为第一位拥有重罪犯身份的美国总统。
在“三大案”中,“颠覆案”和“封口费案”都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惯例。纳瓦罗在被判入狱时,法官就反复强调他是行政豁免权无法庇护的白宫高级顾问。更不用说,特朗普本人也在大选前夕被判有罪,虽然不必服刑且仍可上诉,但这无疑是对特朗普个人的侮辱。“通俄案”不是政治清算但更加恶劣,因为此案发生时特朗普依然在台上掌握着行政权力,但是这给他的教训可能更为深刻。那就是,如果不能牢牢将行政机构掌握在自身手中,那么即使通过选举掌握了政权,也会处于“被清算”的被动位置,遑论畅通无阻地推行自身政策。
政治清算循环的终局:形成“白宫魔咒”并非不可避免
过去八年,美国政治清算的异变愈加明显。因此一个合理的假想是,继韩国总统的“青瓦台魔咒”之后,可能也会出现美国总统的“白宫魔咒”。然而,从坏的一面看,“青瓦台魔咒”的存在表明,韩国政治的极化非常严重,政治斗争极为尖锐,国家政策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都没有稳定的方向;但是从好的一面看,“青瓦台魔咒”能够存在本身也可以说是一项政治成就,那就是在存在“魔咒”预期的情况下,韩国的政治领导人居然能够接受在选举政治中“认赌服输”。 然而,尹锡悦颁布戒严令、试图以行政权力和武力终止国会和反对党活动的做法表明,“青瓦台魔咒”必然是不稳定的。如果真的形成了“白宫魔咒”,恐怕美国的第二次内战也相去不远。
不过,当前看来,美国政治清算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是民主党试图用法律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甚至真的将政治问题理解为了法律问题,结果不仅没能达到打压特朗普的目标,反而起到了动员后者基本盘的反作用。实际上,这一道理也适用于共和党和特朗普。在此次大选中,特朗普之所以能够获得重大政治胜利,也是因为大量中间选民因为通胀问题倒向了共和党,而非MAGA运动(即“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基盘真的有了迅速扩大。就此而言,特朗普在推动激进复仇议程的过程中,就可能遭遇严重的政治麻烦,其未来能否真的全面兑现“复仇议程”、战胜“深层国家”也颇值得怀疑。
从民主党方面来看,在2024年大选的最后关头,其应该也认识到了,想用司法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只会适得其反。因此一直拖延对特朗普的判决,直到后者就职前才做出了有罪但无须服刑这样“高高拿起、轻轻放下”的决定。实际上,在2021—2024年间,拜登个人很可能还多次为针对特朗普的政治清算踩刹车,没有过于穷追猛打。在2025年的新总统就职仪式上,拜登表现得也要比2021年的特朗普更有风度,明显向后者示好。考虑到特朗普主义未来可能盛极而衰,民主党的内斗方法可能更加成熟有效,那么美国政治清算的螺旋恶化循环仍有被暂停的可能。
(肖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外交政策研究室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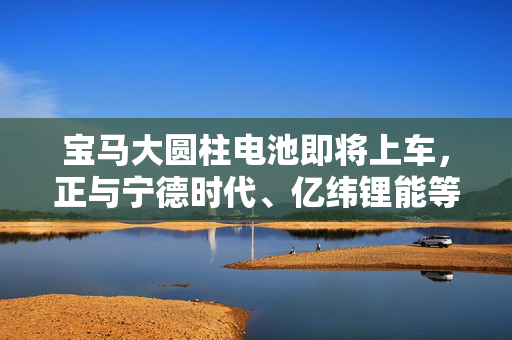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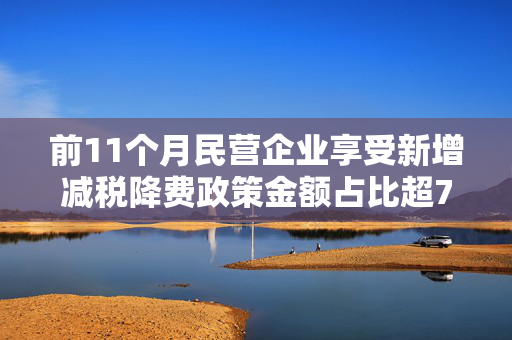







有话要说...